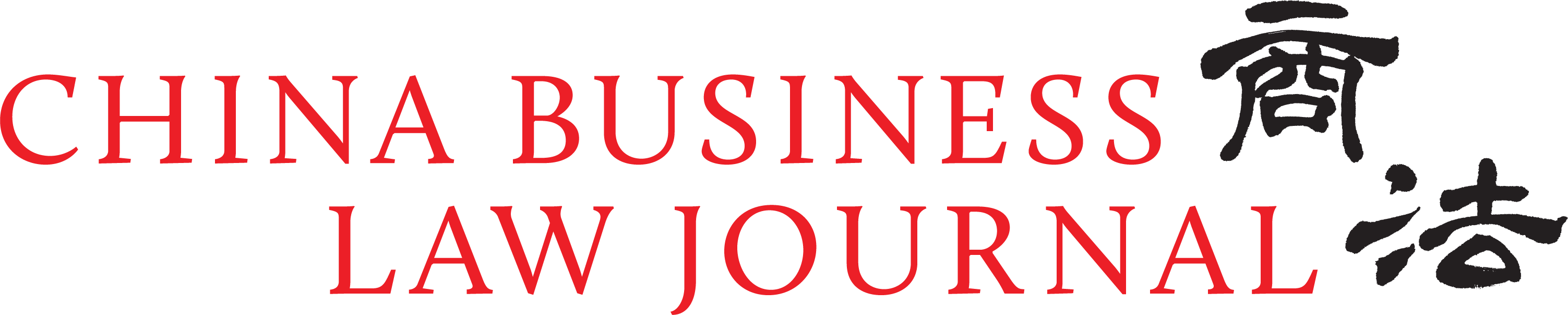LEXICON专栏曾探讨过与专家证据(如《商法》第10期第4辑文章《专家证据》)和法庭文化(如《商法》第11期第3辑文章《法庭中的文化因素》)相关的话题。本期专栏节选自作者近期所作的一个关于文化和语言在民商事纠纷中的影响的演讲。演讲在新西兰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研讨会由新西兰亚洲律师协会和新西兰法律协会主办,围绕着亚洲律师职业和涉亚诉讼展开,新西兰首席大法官Helen Winkelmann参加了研讨会。
专家证人的作用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在这方面的工作。我既作为外国法(包括中国法)专家受邀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庭担任过专家证人,也作为澳大利亚法律专家在外国出庭担任过专家证人,而我作为专家证人提供的所有与文化和语言多样性问题相关的证据都是在上述工作场景中提供。我在多个管辖区参与过各种纠纷案件,做过大量专家证据方面的工作。我经常提供关于外国法律和外国法与国内法交汇的专家意见。
除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庭作专家报告外,我也曾在一个大陆法管辖区作为专家证人出庭。这一工作经历让我有幸体验到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不同,稍后我会分享一些这方面的体会。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的专长是在法律语境下评论文化和语言,比如,如何通过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用词或者与合同关系相关的证据来推断当事人意图。
然而,在非法律语境下或者在没有背景信息的情况下评论文化却不是我所长。这是因为,对文化和语言的审视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下展开,而对我而言,我的专长是在法律语境下提供意见。几年前,我收到一个刑事案件的邀约,要求我提供文化方面的专家证据。这个案件中,一位在墨尔本的亚洲学生被指控通过诈骗钱款参与赌博活动。为争取减刑,被告辩称他参与赌博的目的是筹集资金偿还父母提供的教育费用贷款,父母要求他品学兼优,他一直压力很大,他的行为背后有文化因素的影响。我拒绝了这个邀约,因为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在非法律语境下评论文化问题。
文化的相关性
但首先应该回答一个问题 – 文化在法律语境下是否相关?如果是,这一相关性又如何体现?我想起现澳大利亚联邦法庭法官兼行政上诉审裁庭主席Emilios Kyrou法官的观点,他认为审判人员有必要建立一个“文化心理预警系统,让他们在文化因素起作用的情况下有所警觉,从而积极考虑应该如何应对。”这些观点引申出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化在某些情况下对证据的评估具有重要性,但在某些情况下,文化与证据的评估没有任何关联。
我认为,律师们同样应该建立起这样一个文化心理预警系统,对文化因素的关联性产生警觉。
从我的经验来看,“文化”和“文化差异”通常在以下场景被提及:从主流文化的角度很难理解当事人的行为以及用以描述他们之间的合同关系的语言。
但在现实中,还有更多具体的影响因素,包括语言的使用,法律和商业惯例和理念的差异。这些因素,尤其是语言,带来的潜在影响巨大,已无需多言。
如果争议当事人来自亚洲,识别和理解这些差异本已不易,那么包括合同在内的书面文件,以及可靠的当代文档记载的缺乏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因此,我对专家证人的建议是:识别出这些差异,并判断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否与“文化”有关(按照对 “文化”一字的广义理解),或者,与案件和涉案当事人的特定因素相关,比如他们的语言和商业惯例。
从这方面看,在当事人来自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的案件中,证据关联性和可采性的甄别过程与其他案件无异。关键在于甄别和理解当事人进入商业关系的背景,避免从“主流文化”的角度,或从以普通法为中心的角度做假设或推断结论。而专家的作用就在于此。
文化和语言具有关联系的案件
在今年早些时候,我作为专家证人参与了一个案件,案件最终和解。争议涉及从事代购的澳大利亚公司。当事人在中国境外为居住在中国的人购买产品。购买产品并安排出口到中国的人是买方的代理,不是卖方或出口商的代理。代购牛奶和婴幼儿配方奶粉等产品是极为常见的模式,利润极高。
在这个争议案件中,只有其中一方当事人是从事代购的这些公司的正式所有人。因此,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否构成雇佣关系,亦或是合伙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性质对于判断当事人是否有分享利润的意图非常重要。和其他很多案件一样,在这起案件中,当事人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因此没有证据证明这种合同关系的性质。双方之间的安排都是用中文通过口头判断达成,而证明谈判的惟一记录证据就是微信对话。
其中尤其重要的一个记录是,双方当事人都提到了“咱们的公司”。此外,在我的专家报告中,我还提到一点,即当事人所用的“咱们的”与另一个正式词——“我们的”含义不同。而这一点之前没有被任一方当事人或律师注意到。来自中国的某些地方(包括北方)的人在说“咱们”时,通常包括听者。因此,当他们用“咱们的公司”时,他们指的是说话人和沟通对象共同拥有的公司。
另一方面,当公司的某个员工和其他员工谈论公司时,他们通常使用正式词——“我们”,即“我们的公司”,而不是用“咱们的公司”。在我看来,这就进一步印证了一个推论,即,当双方都使用“咱们的公司”时,他们指的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公司,而非其中一方拥有的公司。
有时候,某个问题被认为是语言问题,但其实这个问题也有文化元素。上述案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人使用语言的习惯不同。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个案件最终进入庭审,专家会就这个问题接受盘问。
在这个案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即当事人都称呼对方为“兄弟”。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即这个词能否说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在我的专家报告中,我提出,这个词用在很多场景,包括有血亲的亲人之间和有“深厚友谊”的人之间。
这个词无法提供更多线索。但我认为,这个词的使用确实说明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等级关系,也不大可能存在类似于雇主和雇员这样的上下级关系。
聘请专家证人的流程
现在,我想评论几个与聘请专家证人的流程相关的问题。
首先,外国法专家证人所提供的证据必然取决于当事人的律师要求专家证人考虑的问题。因此,必须确保律师拟提问的问题的性质在专家证人的专业能力范围内,并确定这些问题足够宽泛,让专家能够应对与更广泛的因素——如文化和语言——相关的问题。正如我此前提到的,外国法专家证人应首先将文化证据定位在广泛的法律语境下。
普通法有一个原则,专家证人不能就必须交由法庭裁决的问题发表意见。专家证人必须牢记于心。换言之,如何适用证据来裁决涉案的实质性问题是法庭的工作,专家证人不得就此发表意见。
一旦发表了此类意见,对方当事人极有可能以专家意见不可采信为由提出异议。这就要求专家证人,尤其是外国法专家证人谨慎,通常使用恰当的措辞即可避免争议。
正如我提到的,我在普通法和大陆法管辖区都做过外国法专家证人。在大陆法管辖区,外国法被视为法律问题,而非事实问题。因此,与在普通法管辖区的地位不同,外国法律并不是必须由当事人提交的专家证据证明的东西。在大陆法管辖区,外国法下的问题由法庭决定。
在我受聘作为澳大利亚法专家证人的大陆法管辖区,我是由法庭聘请的。这就要求我自己甄别专家报告应涉及哪些问题,法庭应该问我哪些问题。在普通法管辖区,专家证人由当事人聘请,而在大陆法管辖区,专家证人的工作范围更开放,我确实需要考虑法庭会如何适用法律来裁决争议中的实质性问题。
第二个我想提及的与聘请流程相关的问题是专家证人提交的针对文化和语言问题的专家报告应该以证据为基础。文化或语言问题与技术性的法律问题一样,都需要支持性证据。
当然,在这一方面,专家证人可依赖自己的经验。但对于文化相关的问题,专家证人应尽可能引用支持性证据。
我曾参与新加兰高等法院的一个案件。在这个案件中,一位新西兰公民未留下遗嘱而身亡,他第一任妻子的亲属和第二任妻子的亲属均要求继承他的土地、财产和公司所有权。
除涉及遗嘱继承的适用法这种技术性法律问题外,我还被要求就中国的遗产规划相关的文化惯例和文化与法律背景提供意见。我在报告中提出,在中国,存在一种厌恶遗产规划的文化,同时我引用了我的职业经验和关于这种文化厌恶的学术和专业评论加以佐证。我的意见支持第二任妻子提供的证据,即在中国文化中,夫妻间讨论彼此遗嘱的现象并不常见。
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专家证人引用的材料是外文材料,对方当事人可能要求提供完整的翻译。因此,对外文资料的引用必须谨慎。因为在专家证人引用的源材料中,大量内容并不相关,完整的翻译耗时,且浪费资源。
最后,我注意到,如果案件进入庭审,专家证人要接受盘问,那么关于外国法律的专家证据极有可能引出更广泛的问题——涉及到文化或其他方面的问题。
几周前,在新南威尔士最高法院的一个案件中,我与对方当事人的专家证人一同出庭,提供并行证据,澳大利亚人称这种情景为“热水浴池”。这个案件涉及中国规定对备用信用证的应用。
尽管这些问题是非常技术性的问题,但法庭提出了与中国司法实践和更广泛的背景相关的问题。因此,我认为,专家证人必须意识到潜在的文化关联性,即使我们被要求发表意见的正式问题中并不包含文化问题,但这些问题可能与文化相关联,而专家证人必须作好准备,就文化影响发表见解。

葛安德目前是世界银行一个工作小组的成员,为亚洲某央行提供职能改革方面的咨询。他曾在上海以外国律师的身份执业(1996-2006),而后回到母校澳大利亚墨尔本法学院从事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2006-2021年)。葛安德现在是墨尔本法学院亚洲法律中心的荣誉首席研究员,亦在多家机构担任顾问,其中包括年利达律师事务所、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和世界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