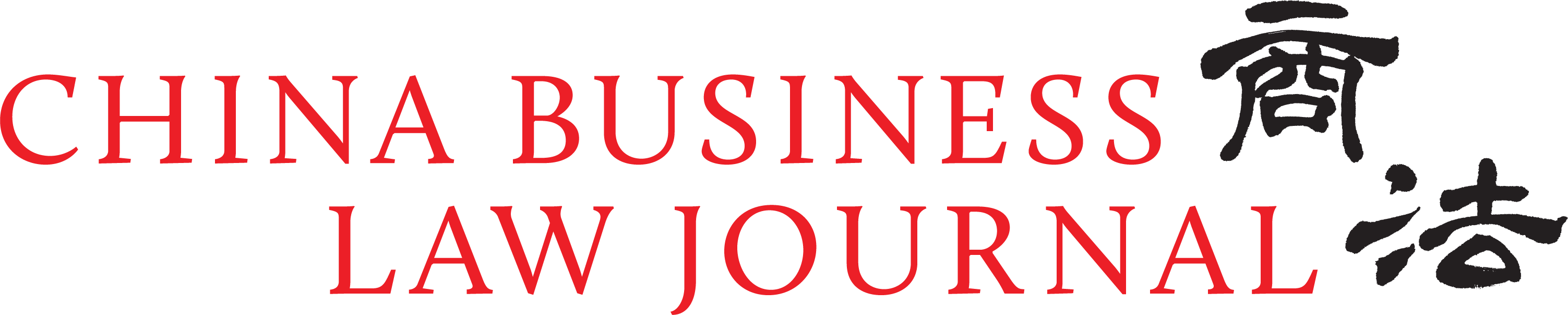一些仲裁机构最近基于双边投资协定作出的裁决可能赋予跨国投资者许多其未曾意识到的权利。作者:Paulo Fohlin
对于任何在海外开展业务或收购境外公司股权的个人或公司来说,双边投资协定所提供的保护具有潜在的重要意义。而且最新的形势发展表明,无论是投资海外的中国投资者,还是投资中国的海外投资者,投资协定对他们的保障变得越来越重要。
自1998年以来,中国已经签署了约25个“新型”双边投资协定与双边贸易协议。在这些协定中规定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赋予投资者在其认为东道国违反协定或协议中所作承诺时,对东道国提起仲裁的权利。
但是,根据中国早期与100多个国家缔结的“旧式”投资协定(其中大多数现今仍然有效),缔约国的投资者并没有这种不受限制的针对东道国提起仲裁的权利。然而不久前,两家仲裁庭根据有关双边投资协定(有关投资协定分别是西班牙与俄罗斯之间、中国与秘鲁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作出的裁决表明,即使是根据中国的“旧式”投资协定,投资者依然可以受到很大的保护。两个仲裁庭独立作出各自的裁决,而且不约而同地一致认定:即使根据“有限制(争议事项)的”仲裁条款,他们对于上述指控东道国征收投资者资产的争端仍具有管辖权。而这些争端涉及的“有限制(争议事项)的”仲裁条款跟中国很多“旧式”的投资协定里的仲裁条款颇为相似。
对于受“旧式”协定保护的投资者来说,同样是由这两家仲裁庭对于最惠国待遇条款所作出的解释,对于他们在与东道国发生争端时是否有权诉诸仲裁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实质性保障
投资协定中包含一系列保护缔约国投资者的条款,以保障他们在东道国的投资不被征收或因其他类似的措施蒙受损失。这些保护性条款及其措施有时被称为“实质性保障”。
投资者有权因其资产被征收而获得合理的补偿,这是实质性保障的核心内容。正如“投资”这一概念一样(见第53页的《旨在鼓励投资的协定》一文),“征收”这一概念涵盖的范围通常很广,不仅包括对财产所有权的正式或直接的征收或国有化,还包括具有同等效果的其他征收形式(通常称为间接征收)。此外,由于对“投资”所作的定义较为广泛,其他类别的投资权利(例如合同权利)也属于可能被征收的投资范畴。这种情况常见的例子是:几个不同国家机关的行为共同导致投资者对其投资的权益被剥夺,而此时东道国是否具有故意,或是否会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并非构成征收的必要条件。举例来说,东道国撤销投资者的经营许可、过度征税、干预合同权利等,都属于对投资者其他形式投资权利的征收。
如果投资协定中没有规定投资争议所适用的仲裁条款,当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被征收或其合法权利遭受侵犯时,要解决因此与东道国之间引发的争端,投资者就不得不寻求当地救济措施 — 要么经由法院,要么经由行政机关 — 而这还得取决于当地是否设有这些争议解决机构。然而,投资者显然对寻求当地救济这一方式不大感兴趣,尤其当他们怀疑东道国政府是否心存善意、当地法院或相关机构是否公正独立时。(有关双边投资协定通常涵盖的保护措施的概述,请见第56页的《双边投资协定的常见条款》。)
程序性保障
除了实质性保障之外,投资协定通常还包含以仲裁条款的形式出现的“程序性保障”措施(也有极少数例外),投资者可据此对东道国提起仲裁程序。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的(争议事项)适用范围在不同的投资协定中不尽相同。但是通常情况下,如同新型的中国投资协定里所订明的那样,这些条款都适用于东道国不履行投资协定中的实质性承诺的行为,以及对这种行为造成的损失的计算。例如,被称为2003年“范本”的中国新型双边投资协定里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规定的争议事项范围就包括“与投资相关的……任何法律争端”。
这种与2003年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中规定相似的,不限制具体争议事项的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解决仲裁条款在中国与多个国家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中都有订明。这些国家包括巴巴多斯(1998)、博茨瓦纳、文莱、约旦、特立尼达、圭亚那、科特迪瓦、吉布提、荷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德国、芬兰、伊朗、贝宁、韩国、俄罗斯联邦、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西班牙、瑞典(1982年缔结双边协定,2004年以协定书方式进行补充)、法国、捷克共和国和印度。该类仲裁条款也出现在中国最近与巴基斯坦、新西兰和新加坡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与投资相关的章节中。
然而,有时候这些投资协定中规定的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制的,比如在中国旧式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情况。例如中国早期与澳大利亚、阿根廷、保加利亚、丹麦等国缔结的旧式双边投资协定中,规定仲裁事项应当是“有关征收补偿金额的纠纷”。
显然,这些限制争议事项的仲裁条款除了适用于东道国“进行征收必须给予合理补偿”的承诺之外,并不适用于因东道国违反其他承诺的争端。因此,“公正和公平地待遇”、“充分的保护和保障”、“不使投资者或其投资遭受任意性或歧视性对待”这些投资协定中常见的东道国对投资保护的承诺将被排除在这类仲裁条款的仲裁适用范围之外。(见第56页的《双边投资协定的常见条款》。)
一些研究人士有时还会进一步假设:类似中国旧式投资协定里出现的限制性仲裁条款将不适用于有关征收是否发生的争议,而只适用于征收事实已确实发生时,有关征收补偿金额的争议,或有关东道国适格的法院或机构已确定事项的争议。然而,对于这种假设,也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对其提出质疑。
旨在鼓励投资的协定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至少有180个国家相互间签署了共约3000个双边投资协定。1990年以前,世界上只有约400个双边投资协定;但是1990年以后,各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数量大幅增加。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缔约国双方相互承诺,东道国将“公正与合理”地对待来自另一缔约国的投资者,不得采取歧视性措施,不得在未给予合理补偿的情况下,对缔约国投资者的投资实施征收或国有化。对于投资者提出的东道国违反了协定中保护投资者的承诺的指控,双边协定中一般都规定有投资者可以针对该东道国提起仲裁程序,交由位于第三国的中立的仲裁庭进行裁决。在这些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仲裁程序中,投资者还可以援引适用国际公法(即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的一些规则,而这些规则一般情况下只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争端。
双边投资协定的宗旨,正如在其序言中通常所阐述的,在于为缔约国双方的投资者在另一缔约国的投资创造有利的环境。有的双边投资协定中还会强调,其宗旨在于保护外国投资者避免政治风险(相对于商业风险而言),尤其是当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因为这些国家对外国投资的立场很可能因政权交替等情况而发生变化。与此相对,在有的双边投资协定中,东道国会强调该国在外商投资方面具备良好的政府监管与完善的法律制度,从而使自身成为受外国投资者青睐的投资目的地,并且有利于引进更多外来投资,包括资金、管理技术、专业知识等。
要想得到投资协定的保护,其中一个缔约国的投资者(包括个人或公司)必须要在另一缔约国(即东道国)进行了“投资”(即属于该协定中所定义的投资)。通常,双边协定中对“投资”的定义较为宽泛,而且往往列举一部分属于“投资”的交易类型,例如表述为:“投资”可指任何类型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动产与不动产、公司股份或其他形式的权益、具有经济价值的合同权利、以及知识产权等等。上文所述的西班牙投资者诉俄罗斯联邦的投资争端仲裁案中有关管辖权的裁定就为“投资”所涵盖的资产形式提供了一项新的案例。仲裁庭认为西班牙投资者从俄罗斯境外市场购得的俄罗斯Yukos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ADRs),也属于西班牙与俄罗斯投资协定中所指的“资产”。
中国投资者基于旧式投资协定提起的投资争端仲裁
尽管中国拥有大量的外国投资,也与众多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但是至今尚未有报道在任何有关中国大陆的投资协定下,中国作为东道国被提起投资争端仲裁。但是,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目前受理有一起中国投资者依据中国与秘鲁1994签订的旧式投资协定对秘鲁提起的投资争端仲裁,该纠纷自2007年至今仍未结案。(案名:Mr Tza Yap Shum v Republic of Peru,ICSID 案号:ARB/07/6;请参阅以下网址 http://www.worldbank.org/icsid, http://ita.law.uvic.ca,以及投资协定相关新闻(2007年3月2日)。)
在中国与秘鲁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适用于“对征收补偿金额的纠纷”。该投资协定中同时也包含最惠国待遇条款。据称,该中国投资者因其间接持股90%的一间鱼粉公司被秘鲁政府间接征收,因此主张2000万美元的补偿金。
秘鲁的国税局指控该鱼粉公司拖欠税款。而据该投资者所述,他的公司第一次收到欠税通知书后仅仅一个月,秘鲁的税务局就将其公司的银行存款查封没收,而此时仍处于法定的申诉期间,而且他的公司也正在试图对欠税指控提出申诉。这名中国投资者声称,对其公司银行存款的查封没收导致公司营运瘫痪,构成征收事实,但是秘鲁政府却并没有根据双边投资协定的规定作出赔偿。
ICSID的仲裁庭曾于2009年6月对此案的管辖问题作出过决定。根据该决定,投资者的赔偿请求是基于秘鲁违反了投资协定中的以下条款:
(1) 征收;
(2) 公平和公正待遇;以及
(3) 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允许投资者自由转移资金。
就秘鲁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仲裁庭认定:中国与秘鲁双边投资协定中限制争议事项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的适用范围涵盖了“是否存在征收事实”的争议。因此,该仲裁庭认为其对于秘鲁政府是否实施了间接征收行为这一问题拥有管辖权,而不仅仅是决定补偿金额应为多少。
然而,当秘鲁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后,仲裁庭在研究了秘鲁与中国的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条款以及秘鲁签订的另一份投资协定中的不限制争议事项的争端仲裁条款后,却认为该庭没有裁定秘鲁是否违反了投资协定中的“公平和公正待遇”以及“保护投资者的投资,允许投资者自由转移资金”规定的管辖权。
秘鲁提出的反驳还包括,该案中的仲裁申请人并不符合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投资人”资格,因为尽管他是中国内地公民,但同时还是香港居民。但是仲裁庭认为申请人符合“投资人”资格,因为协定并没有将居住在香港的中国公民排除在“投资人”之外。
对旧式协定中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的解释
上述于2009年6月由ICSID就中国与秘鲁投资协定下的投资争端作出的裁定,对确定中国签署的旧式投资协定里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的适用范围有着直接的影响。近期就有一家仲裁庭根据西班牙和俄罗斯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做出了类似的裁决(案名:Renta 4 et al v the Russian Federation)。该裁决是于2009年3月在瑞典做出的,中国投资者诉秘鲁政府案中的当事方和仲裁庭显然并不知道该裁决。但是,两个仲裁庭对各自案件中的争端仲裁条款管辖范围的解释所依据的理由却颇为相似。
西班牙和俄罗斯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适用于“本协定第六条中关于征收补偿金额及补偿金支付方法的任何纠纷”。经过仔细和深入地分析后,该案的仲裁庭认为根据这一仲裁条款,该庭拥有裁定是否发生了征收事实的管辖权,而不仅限于裁定征收补偿金的数额。
在分析并得出他们各自的仲裁决定结论的过程中,两家仲裁庭对于其他仲裁机构先前作出的与他们的结论相反的裁定,提出了批评,特别是认为先前的裁决忽略了对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适用范围的分析。但俄罗斯联邦政府现正申请瑞典法院作出一项声明,认定该仲裁庭对西班牙与俄罗斯投资协定项下的争端不具备管辖权(本文的作者在此法院程序中担任西班牙投资者暨被申请人的辩护律师)。而与此同时,本案的仲裁程序仍在进行之中。
双边投资协定的常见条款
除了本文的正文中所提到的关于征收的保护之外,双边投资协定通常规定东道国应当给予投资者和/或及其投资以公平和公正的待遇。东道国的法院或行政机关不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和/或执法不公,都可被视为违反了这一规定。双边投资协定里通常还会进一步规定东道国为投资者提供全面的保护和保障,这其中包括对投资者的厂房、营业场所的保护。此外,东道国往往还会承诺不对投资者实施任何任意性或歧视性的措施。
双边投资协定中通常还会规定有“保护伞条款”,即东道国承诺将遵守其对投资者直接作出的任何承诺,例如东道国的官员或政府机构与投资者直接签订的合同里所作出的承诺。因此,原则上说,一旦东道国违反了其与投资者签订的此类合同,也会构成对双边投资协定的违反。尽管大部分公司都不会直接和东道国的政府签订合同,但保护伞条款为那些签署了该类合同的公司提供了额外的保护。除此以外,双边投资协定中通常还有对“投资和收益的汇回”的规定,即东道国保证投资者有权将其投资利润和收益以转换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形式。一般情况下,协定里还有“国民待遇”条款,保证缔约国的投资者在东道国应当
享有和东道国国民相同的待遇。但是,在中国大陆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中国并不全面履行该义务。
对于受中国旧式投资协定保护的投资海外的中国投资者,以及投资中国的外国投资者来说,双边投资协定中包含的最惠国待遇条款(MFN条款)尤其值得关注。简单来说,最惠国待遇条款是指东道国给予缔约国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其他任何第三国的投资者的待遇。最惠国待遇条款所带来的主要问题是,这些条款中所指的“待遇”是否涵盖实质性保障以及程序性保障。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请见正文中“对中国旧式协定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一节。
对中国旧式协定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
以上分别基于西班牙和俄罗斯,以及中国和秘鲁之间双边投资协定,于2009年作出的两案裁决的另一重要影响,可能在于中国旧式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允许投资者依据东道国与其他国家投资协定中的不限制争议事项的争端仲裁条款,就旧式协定中限定的争议事项范围之外的其他事项提交仲裁。最近 John Savage 和 Elodie Dulac 合写了一篇文章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而这两名作者在撰写文章时并不了解2009年这两起案件的仲裁裁定。(文章名称为《中国的投资保护协定以及其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带来的争端解决机遇),发表于2009年10月的《斯德哥尔摩国际仲裁评论》)。
Savage 和 Dulac 解释说,中国的旧式协定中一般都规定有最惠国待遇条款,规定东道国对待另一缔约国的投资者和/或他们的投资的待遇,应不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及其投资的待遇。
投资争端仲裁适用的程序规则
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通常规定投资者可将投资争议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仲裁,或者根据1976年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UNCITRAL仲裁规则)提交临时仲裁庭仲裁。有时候,投资者会选择机构仲裁规则,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或者在极少数情况下,选择其他机构的仲裁规则(如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等)。
如今绝大部分的投资争端都交由 ICSID 仲裁。在 ICSID仲裁中,对于裁决以及其他事项的异议,不适用任何国家的国内仲裁法,在这一点上可以说 ICSID 仲裁没有“仲裁地”的概念。相反,当事方如对裁决有异议,必须依 ICSID 公
约的规定提出申请,继而由按照 ICSID 公约的规定成立的临时专案委员会来对该异议作出裁定。对于投资争端的仲裁,除了 ICSID 仲裁以外,瑞典据说是最常见的仲裁地,具体表现为根据 UNCITRAL 仲裁规则的临时仲裁,或者是瑞
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
过去,中国不太愿意在其签署的投资协定中规定 ICSID仲裁,而倾向选择根据 UNCITRAL 仲裁规则的临时仲裁,或根据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的机构仲裁。中国新型的双边投资协定允许投资者选择提交 ICSID 仲裁或根据UNCITRAL 仲裁规则的临时仲裁。中国已经签署了《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ICSID公约),并且该公约已于1993年对中国生效,但根据中国作出的一份通知,中国声明仅考虑把“由征收和国有化而引发的有关补偿的争议”提交 ICSID 管辖。但在本文正文中讨论过的、根据中国和秘鲁之间投资协定作出的裁决,支持了“该通知并不能限制仲裁庭对中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有关争议拥有管辖权”的观点。
Savage 和 Dulac 在文章中还阐述,从2000年“Maffezini诉西班牙”投资争端仲裁一案以及其后的一些案例中都可看到,仲裁庭对相关协定中最惠国待遇条款里“待遇”一词范围的解释并不限于投资协定中的实质性保障条款,同时还包含表现为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的程序性保障条款,除非协定中另有约定。这种解释将使投资者能够利用最惠国待遇条款来援引东道国与别国签署的投资协定中的不限制争议事项的仲裁条款。但另一方面,Savage 和 Dulac 也提到,在其他几起投资争端仲裁案中(其中,2005年 Plama 诉保加利亚一案为首起作出此类裁决的案例),仲裁庭裁定只有投资协定中清楚明确且毫无歧义地作出相应的规定,最惠国待遇条款中的“待遇”才可以引申至申请仲裁的权利。
2009年3月根据西班牙和俄罗斯投资协定作出的的仲裁裁决中,仲裁庭一致认为,最惠国待遇条款中的“待遇”原则上应包含实质性保障与程序性保障。因此,在投资协定中无须明确说明最惠国待遇条款可以引申至东道国赋予别国投资者更广泛的仲裁权利。其中一名仲裁员强调:Plama 诉保加利亚一案所确立的原则,即投资者根据最惠国条款主张更广范的仲裁权利必须在相关投资协定中清楚列明的要求,不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解释之通则”的规定。正如对于国际条约的其他条款一样,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既不能过于严格,亦不能过于宽泛。但是,在2009年3月所作出的裁决中,仲裁庭的大多数成员认为,由于西班牙和俄罗斯的投资协定中有关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限制性表述,该条款中的“待遇”并不包含提请仲裁的权利。
同样地,从2009年6月根据中国和秘鲁投资协议作出的裁决可以看出,原则上,仲裁庭认定最惠国待遇条款中的“待遇”包含实质性保障与程序性保障。该项裁定所依据的理由也跟2009年3月根据西班牙和俄罗斯投资协定作出的裁决理由相似。该案的仲裁庭指出,中国和秘鲁投资协定中有关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表述并没有对“待遇”的范围作出限制。与西班牙和俄罗斯的投资协定一样,中国和秘鲁的投资协定里有关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措辞和一些中国旧式投资协定里的表述类似。
但是,仲裁庭认为中国和秘鲁投资协定里的以下具体表述排除了投资者援引其他协定中范围更广的仲裁条款的可能性:“(有关征收补偿金额以外的)其他争议,在当事各方同意的情况下可提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仲裁庭认为,这一条具体规定的效力优先于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一般表述。因此,由于秘鲁不同意由 ICSID 和该仲裁庭处理投资者对秘鲁政府违反“公平和公正待遇”以及“保障投资者的投资,资金可自由转移”的指控,审理该案的仲裁庭最终认定自己对这些事项没有管辖权。
无论是2009年上述两起案件中仲裁庭的裁决,还是2007年根据英国与俄罗斯投资协定处理的 Rosinvest 诉俄罗斯联邦一案的仲裁庭裁决都没有认定:最惠国待遇条款如欲延伸适用于投资者提请仲裁的权利,则必须在投资协定中具体列明。
在上述2007年作出的裁决中,仲裁庭认定: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以及俄罗斯与别国签订的另一份投资协定中的不限制争议事项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该仲裁庭对有关争议享有管辖权。但是,俄罗斯联邦已经针对该仲裁庭在英国与俄罗斯投资协定下的管辖权事宜,在瑞典法院启动诉讼程序。
可仲裁事项范围扩大?
总的来说,受中国旧式投资协定保护的许多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不应想当然地排除将其与东道国投资争端中的责任追究以及责任数额纠纷提起仲裁的可能性。这不仅适用于在海外开展业务或拥有海外公司股份或类似权益的中国投资者,也适用于在中国开展业务或在中国拥有相关权益的外国投资者。
首先,这些旧式协定中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可能允许中国和外国投资者就东道国是否征收了他们的资产这一争议提请仲裁,而不仅限于征收补偿数额这一问题。
其次,这些旧式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结合东道国与别国签订的不限制争议事项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可能赋予中国和外国投资者就东道国违反协定中实质性保障条款(包括征收条款)以及因这些违约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金额等相关争议提请仲裁的权利。据此,投资海外的中国投资者可以利用旧式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来援引东道国与别国的投资协定中适用范围更广的仲裁条款来为自己争取权益。同样地,投资中国的海外投资者也可以利用旧式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来援引中国新型投资协定里不限制争议事项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条款来保护自己。
双边投资协定的法律依据
要全面了解双边投资协定及其潜在的法律后果,仅阅读和理解其条文内容是不够的。双边投资协定通常是较为概括性的文件,篇幅大概5到10页左右。很多在投资纠纷中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在投资协定中却并未提及。
如何正确解释投资协定中的条款,也是一个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该类争议可能和国际公法领域的许多基本法律有关。除了常设仲裁法院、国际常设法院、国际法院等各种裁判机构根据这些基本法律所作出的裁决之外,还有大约300个公开的有关投资协定争议的仲裁裁决。这些裁决大部分都是根据《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ICSID公约)中的程序规则作出的。进行投资争端仲裁时经常会援引适用这些程序规则中的有关条款。
《国际法院规约》
国际法对于国家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法律渊源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一款有明确的说明。该条款规定法院在裁判时应适用:
(1)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
(2)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
(3)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
(4)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
双边投资协定就属于上述第(1)项所说的“国际协约”。而第(2)项中的“国际习惯”,也就是常说的“国际习惯法”。在国际投资纠纷中,对于投资协定中没有提及的一些国际惯例是否存在、其内容为何、以及是否适用于诉争案件,也经常是案件中的争议焦点之一。
国家作出的、意在对其具有约束力的的单方面承诺,是《国际法院规约》中没有提及的一种国家义务的法律渊源。该类单方面承诺可以在有关保护外国投资的法律中找到。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与投资协定仲裁相关的法律依据还包括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有关规则。该《公约》可视为适用于国家之间条约的“合同法”,它对于加入该公约的缔约国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但对于没有加入的国家,《公约》则如同国际习惯法一样,不一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该《公约》包括“条约之缔结及生效”、“条约之遵守、适用及解释”和“条约之失效、终止及停止施行”等章节。在处理投资协定纠纷时经常会援引里面的“条约之解释”条款。《公约》第31条“解释之通则”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公约》第27条“国内法与条约之遵守”也是与投资协定息息相关的,即:“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因此,即便是东道国宪法里的规定也不可以作为其不履行双边投资协定义务的理由。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
2001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ILC)通过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简称《国际责任条款》),对投资协定下的争端仲裁也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国际法委员会属于联合国的内部机构,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3条之规定于1948年成立的。尽管不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但《国际责任条款》已被普遍作为国际习惯法而援引适用。《国际责任条款》明确规定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责任。然而根据一篇权威的评论,其中的有关责任条款可能同样也适用于国家对于非国家实体的义务。因此,这些条款对于受投资协定保护的私人投资者来说也是值得关注的。
与投资协定对投资者的保护有关,《国家责任条款》中有关“属于国家行为的行为”的规定非常重要(其中第四条、第五条及其他条款中有相应的规定)。这些条款说明什么样的行为应视为国家行为。当然,原则上,国家只应对其自身的行为负责。首先,国家行为包括任何国家机关实施的行为,不论该行为属于行
使立法、行政、司法职能,还是任何其他职能。因此,对于投资协定中的东道国来说,假如其议会的立法、政府的行为或法院的司法措施违反了投资协定中的有关规定,那么此东道国就可能须为此负责。而这些国家机关实施该行为时是否在行使“政府职能”则并不重要。其次,经该国法律授权行使部分“政府职能”的不属于国家机关的个人或实体的行为,当该个人或实体行使该种“政府职能”时,其行为也应视为国家行为。举例来说,一家国有或非国有的商事公司,如果在从事商业活动之外也行使某种“政府职能”,则其行使政府职能的行为即为国家行为。因此,假如东道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或者上述行使政府职能的个人或实体实施了某一行为或不作为,而该行为或不作为是违反东道国在投资协定中的义务的,那么东道国就须为此负责。此时就进一步涉及到对这些违约行为的救济问题。
《国家责任条款》也规定了有关违反国际义务的救济措施。责任国有义务对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提供充分赔偿,可单独或合并地采取恢复原状、补偿和抵偿三种方式。责任国有义务补偿该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害,如果这种损害没有以恢复原状的方式得到赔偿。这种补偿应该弥补在经济上可以评估的任何损害,包括利润及利息损失(参见第31条、第34条、第36条和第38条之规定)。双边投资协定通常只会就东道国实施的合法征收行为的补偿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而不会就东道国违反协定义务对投资者造成损害时如何补偿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这并不妨碍投资者根据《国家责任条款》确定的国际惯例,要求东道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哥德堡律师是维格律师事务所在香港的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