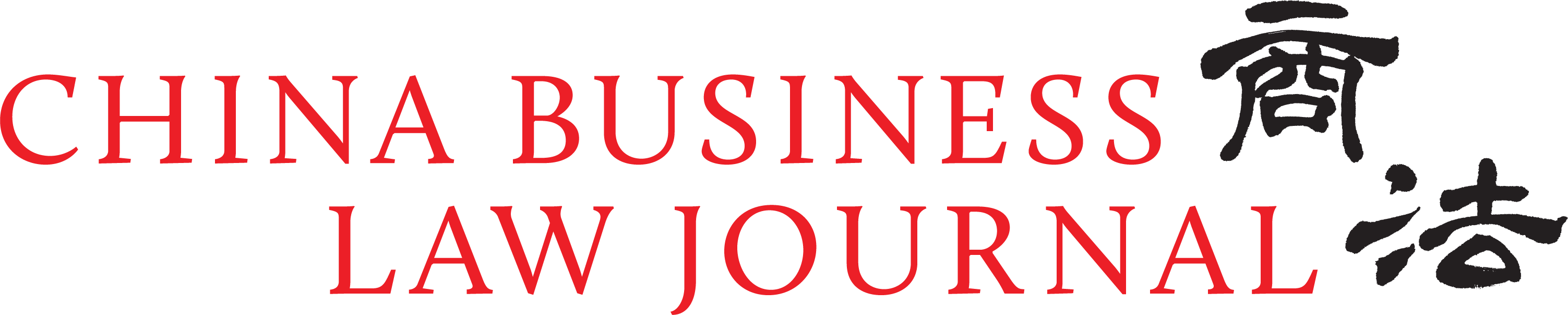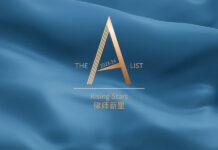国际律师协会反垄断委员会新任联席主席许蓉蓉向张韵凝讲述她开拓中国反垄断律师国际视野的计划,以及在不同执业领域中切换跑道、最终选择反垄断的独特经验

知名律师、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许蓉蓉于今年1月1日起,出任国际律师协会反垄断委员会的联席主席,成为担任反垄断委员会联席主席的首位中国女律师。她与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伦敦办公室的高级合伙人Samantha Mobley共同承担该职务。
国际律师协会于1947年由34个国家的律师协会共同创办,现已扩大为一个拥有190个律师协会及法律学会、与八万名律师会员的国际性法律组织。该协会共分为19个法律领域,反垄断是其中之一。
尽管这项任命认可了许蓉蓉在反垄断领域的地位,但该领域并非她的职业生涯起点,她甚至也不是从律师事务所的初级职位开始法律事业。从香港大学毕业后,许蓉蓉于1990年投身于怡和集团在香港的一家房地产子公司,-担任该公司的独任法务。两年后,她加入Johnson Stokes and Master——该律所后来通过合并成为今日的孖士打律师事务所(Mayer Brown)——并在不久后踏足并购领域。1999年,当香港电信行业因新法规的实施变得炙手可热,许蓉蓉重返法务行列,加入当时香港第二大的固定电话电信运营商九仓电讯。
因缘际会,她搬到中国内地这一在当时不那么发达、但快速发展的法律市场。该举动显得罕见而大胆,并最终巩固了她成为该地区最有经验的反垄断面孔之一的地位。
凭借对本地和国际反垄断事务的深刻了解,许蓉蓉向《商法》分享了她对于中国近期反垄断监管行动最新趋势的看法,以及拥抱变化的人生故事。
《商法》:作为国际律师协会反垄断委员会的新任联席主席,您对自己的新角色有何感想?上任后,您在国际律师协会有哪些计划目标,将加入哪些新元素?
许蓉蓉:我在2010年开始参加国际律师协会,它们在十年前邀请我担任委员。这个协会有一个特点,基本上每一个国家只邀请一个代表,里面的委员每两年就会换一个角色。我加入反垄断委员会的时候是从最初级的沟通委员开始做起,每两年要为委员会做一些贡献,如果贡献不足或者它觉得你能力不强,就会把你淘汰掉。
这一届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从来没有一个中国女律师能够在国际上做这么资深的位置,所以我也觉得非常幸运,特别是我们这一届由两个女律师做联席主席,这在国际律师协会反垄断委员会里也是没有先例的。
所以我也有一些感想。第一,中国律师凭着我们的能力和努力,还是可以在国际平台上做到资深的位置,不要认为中国律师的能力比不上其他国家。第二,女性律师的地位在国际上也是有不断地提升。第三,上任后我与另外一位联席主席也有更多的工作计划:
首先,我们希望能够协助年轻律师更多地了解国际平台,协助他们成长。除了了解自己国家的反垄断法以外,还能够有一个全球反垄断法的视野。我们也在给他们筹备一些免费的培训,包括线上或线下。
其次,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跟国际律师协会沟通,它们希望随着中国放松防疫政策,能够来这里做更多的推广。中国律师以往可能因为语言或疫情的原因,在国际平台上的活跃度相对比较低。我也希望能为中国律师提供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国际律师协会到底有什么不同的业务领域及会议,包括我们其实是有奖学金的,律师无论是写文章或者是做一些专题,如果做得好,我们也会给予奖学金和一些奖励。
我的个人计划可能会超越反垄断委员会,因为我还是另外一个协会Asia Regional Forum——中国工作小组——的一个委员,所以我也希望在之后几年能够在国内进行更多的推广,让不同城市的律师之间有更多的交流,同时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并购、争议解决、合规、房地产等,为我们的年轻律师和中国律师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希望这两年能把这些计划一一落实。其中有些计划其实已经启动了。
《商法》:国际律师协会在76年的历史中,迎来第二位女性主席。您也是该协会反垄断委员会联席主席中的首位中国女律师。您如何看待近年来女律师地位的发展?
许蓉蓉:这是一个比较敏感也很重要的话题,根据我十几年来在国际上的一些观察,我比较惊讶地发现,其实中国女律师的待遇相对是比较公平的,而且地位是比较高的。
相对而言,一些传统国家的女律师地位没那么高,例如日本、韩国,这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原因。但即使在欧洲、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女律师的职业发展也会碰到或受限于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因为我们可能被赋予更多的期待去照顾家庭,所以在大部分国家里,家庭支持方面都没有得到很多的保障。
女律师总是要向家人解释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却不能放更多的时间去发展个人事业。在国外,可能没有祖父母或保姆等资源协助女律师带小孩,所以女律师如果有孩子,可能需要做全职妈妈,事业会暂时中断。或者即便不做全职妈妈,她们也只能兼顾工作,没办法全程投入。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律师协会专门在每一个委员会里安排一个委员来确保有足够公平的机会,除了在性别方面希望给女性更多的机会,也希望确保不同的国家能够有分享到国际律师协会的资源。
其实在中国,我们能够得到的支持和资源相对是比较令人羡慕的。首先中国女律师的人数很多,特别是在法学院或者在工作单位,女律师的比例至少占一半。另外,律所里有不少女合伙人,甚至有些律所的管委会主任也都是女律师,所以相对来说,女性能获得的地位越来越资深。
我希望随着国际律师协会迎来第二位女性主席,包括反垄断委员会也是第一次有两位女律师做联席主席,我们也能够加强这方面的呼吁和影响力,让女性的工作机会更趋于平等,并获得更多资源去支持我们的职业发展。
我觉得世界已经改变了,女性不应该只有单一的角色,我们应该可以承担更多在职业上的任务、对社会作出贡献。
《商法》:随着中国开放市场、融入国际竞争,出现大量海外交叉业务,中国的反垄断法规会出现哪些新趋势?
许蓉蓉:中国的《反垄断法》因为设立的时间相对其他国家较晚,因此大量参考了其他国家的法律进展,尤其是欧盟。中国有自己的法律体系,所以即使参考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规定,也会形成自己的法规和一些理解。
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法可能存在一些空白,或者自身没有太多的案例可做参考。比如说最惠国待遇,即英文的MFN,这个条款在近几年的反垄断法规里有提到,但案例相对没那么多,所以在研究相关问题时,我们会参考外国的规定。
但反过来说,中国的《反垄断法》对境外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例如几年前有一个经营者集中申报“抢跑”行为,由中国作出调查和处罚的先例。这个案子出来以后,欧盟、日本等其他司法管辖区参考了中国的判决,相应受到影响,也开始对同类案件提起调查并作出处罚。
最近,美国对劳动合同里的“不竞争条款/non-compete clause”提出了调查,认为竞争对手之间不能互相招揽员工或者对一些员工设有非竞业的限制也可以从反垄断的角度考虑是否违法。
这属于比较前卫的看法,其实美国已经有几年这样执行的经验,其他国家的反垄断机构都在考虑落实类似的操作,中国在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也会留意到这一全球趋势,从而影响我们的《反垄断法》,包括对劳动合同的规定。
不同法域的法律之间互相影响是常有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留意全球趋势。
《商法》:中国有哪些特定行业经常出现反垄断领域的问题?
许蓉蓉:我觉得跟行业有关,也可以说跟行业没关系。说与行业有关在于《反垄断法》经常强调消费者的利益与民生,如果有某些行业或某些产品出现垄断,很有可能整个行业会被提起调查。
包括近几年对互联网平台的调查,可能更多集中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因为这些平台已经做大做强。事实上,有市场支配地位并不违法,只有在平台二选一、对消费者有歧视性待遇、大数据“杀熟”,才可能引发调查。恰恰近几年互联网平台出现这些情况更多,所以你会感觉好像就针对互联网平台。
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汽车行业,另外一个是药企。你会发现某一段时间对汽车行业和药企的调查也特别多,它们的问题是竞争对手之间有所谓的协同行为。譬如它们对某些原料同时提价或者同时限定产量或销量。这样做对国计民生和消费者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可能监管机构对行业进行比较大量的调查。
但其实严格来说,《反垄断法》是适用于所有行业的。如果某企业或行业被投诉,也会被提起调查,只是这些个案比较少,没有引起大众关注,所以民众产生了误解,觉得只针对某些行业提起调查。
《商法》:今年是《反垄断法》实施的第15年,目前该领域的人才储备与市场需求是否匹配?
许蓉蓉:我觉得这是一个鸡和鸡蛋的问题,还需要两边的努力。
如果企业违反了《反垄断法》,无论是被调查还是被处罚,对企业的影响比较深远。反垄断的问题又往往比较复杂,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需要各个律所的合伙人与客户多做一些推广和沟通,让不同的客户理解反垄断合规的重要性,协助客户建立反垄断合规制度。或者从一些小问题入手,例如销售合同、经销商协议等,希望客户能够理解这些都是反垄断合规方面比较重要的问题。
只有在有需求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能培养年轻律师,让他们增强这方面的业务能力。如果没有适应的业务量,你也没办法去培养,也没办法给律师做储备。但如果坐等业务进来,我觉得可能会有点被动。
《商法》:您的职业生涯始于房地产企业法务,随后一路辗转成为律所的反垄断领域合伙人,中间还一度短暂地重返法务队伍。企业法务和外部律师主要有些区别?法务经验可以为外部律师工作带来哪些裨益?
许蓉蓉:从1990年到1992年,我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了两年企业法务。其实企业对法务的要求更多在于内部协调,我当时应该花了70%至80%的时间在处理这一部分事务,例如不同部门之间的法律问题与矛盾,如何降低风险,反而一些新的法规或者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我都依赖于外部律师提供意见。
工作两年后,我觉得如果长期做下去会越来越轻松,因为内部沟通已经很顺畅,与各部门也建立起信任感,但作为律师的工作能力可能会丧失,所以我想尽快跳出来,重新把律师工作捡起来,否则很难回头。
但我觉得这个经验很可贵。在重返律师行业的最初几年我还是在房地产领域,后来就转到并购。在做并购的时候我觉得这[法务]经验非常重要,因为你能够知道一个法务提出的问题很有可能不是他的问题,是各个部门的问题。外部律师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把所有法律上的技术问题都对客户说了,但是客户只会认为你把这些问题或风险点抛给他,你没有和他并肩作战,或考虑到业务部门的问题一起解决。
所以如果年轻的律师在早年做过法务,这个经验对他们未来当律师或者升任合伙人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商法》:您的执业领域及专注的行业不断出现变化,从房地产、并购、电信业、到反垄断,有哪些原因促成这些转变?每一次转型时,您是否会感到困难?
许蓉蓉:我认为是两个原因,机会与自身的努力。
转换领域要观察市场情况、法律的情况,有没有提供这个机会?如果没有法律或者这个法律不被重视,客户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律师就没有机会去做。
例如香港在1999年才通过新的《电讯条例》,电信行业好得不得了,电信律师特别受欢迎,收入很高,很多律师都想做。同样,内地的《反垄断法》在2008年才生效,在此之前,没有可能成为反垄断律师。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靠自己,不要在固有的领域里限制自己的学习机会,要扩大范围。在房地产行业的时候,我尽所有能力去接触这一行业里不同的问题,曾做过小型诉讼或者小规模的并购。
我在君合律师事务所建立反垄断组时也是一样的道理。2007年国家通过《反垄断法》的时候,管委会主任说需要设立反垄断组。内地律师没有相应的经验,而我在做法务的时候,有30%的业务是处理香港《竞争条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文件。所以君合的管委会主任就说,我们没有律师有相应的经验,你有30%就比其他人好很多,我们就可以用来学习发展。
转型当然有困难,因为我有三年关注的所有法律问题都在房地产方面。并购的经验非常不一样,这个领域的律师可能会涉及不同的行业,从传统的银行、矿,到新兴的半导体、互联网企业。所以我进入并购领域时的困难,就是对不同行业的认识可能不够多,每一次做业务都要重新了解一次。第二就是并购的[业务]能力,除了审慎调查,还有股权转让、劳动法、税法、银行贷款,这些是在做房地产律师时不一定会碰到的。
但如果愿意花费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重新学习,有个资深的律师或者合伙人带着,我觉得上手起来并不困难。
法律知识和能力本身就是跨领域的,只要基本功比较扎实,在换领域的时候相对没有那么困难。我在1999年转做电信行业法务的时候,大概也是花了一年的时间重新学习所有电信法技术层面的问题。
《商法》:2003年,两地推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通过专业资格互认,以促进人才来往。作为早期通过CEPA进入内地法律市场的香港精英,您认为经过20年的发展,两地律界人才流动有哪些变化?
许蓉蓉:2004年,我由于家庭原因需要定居北京,成为第二位通过CEPA来内地工作的香港律师。我感觉最初10年相对是比较寂寞的。当时香港律师来内地工作,更多选择在上海、广州、或者加入国际律所,几乎没有人在内地律所工作。
造成这个情况除了有文化因素,还有两地法律的不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收入。我在当年加入君合的时候,收入是我在香港收入的10%,税也比香港多很多。这会使得很多香港律师感觉来内地发展有不确定性,也面临比较现实的收入问题。所以早年有更多内地律师去香港执业。
但我自己觉得近几年有很大的变化。第一,内地律所的工资越来越高,虽然与香港的收入还有一段距离,但基本上拉近了很多。第二,随着香港回归26年,两地互通,港人与内地的文化、工作、法律、客户的交流更多,排除了一些香港律师过来的担忧。第三,也要感谢国家安排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司法考试。香港律师现在过来内地律所工作,可以通过CEPA与司法考试机制,如果拿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执业]资格以后,在粤港澳大湾区是可以从事大部分的业务,包括诉讼和仲裁。
我觉得还有商业机会,因为现在许多内地企业到境外投资,有不少的交易文件适用香港法,包括争议解决。中英双语在香港法律界都是法定语言,所以香港律师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随着两地加强交流,加上国家的推广,我认为将会有更多的香港律师进入内地从事法律业务。